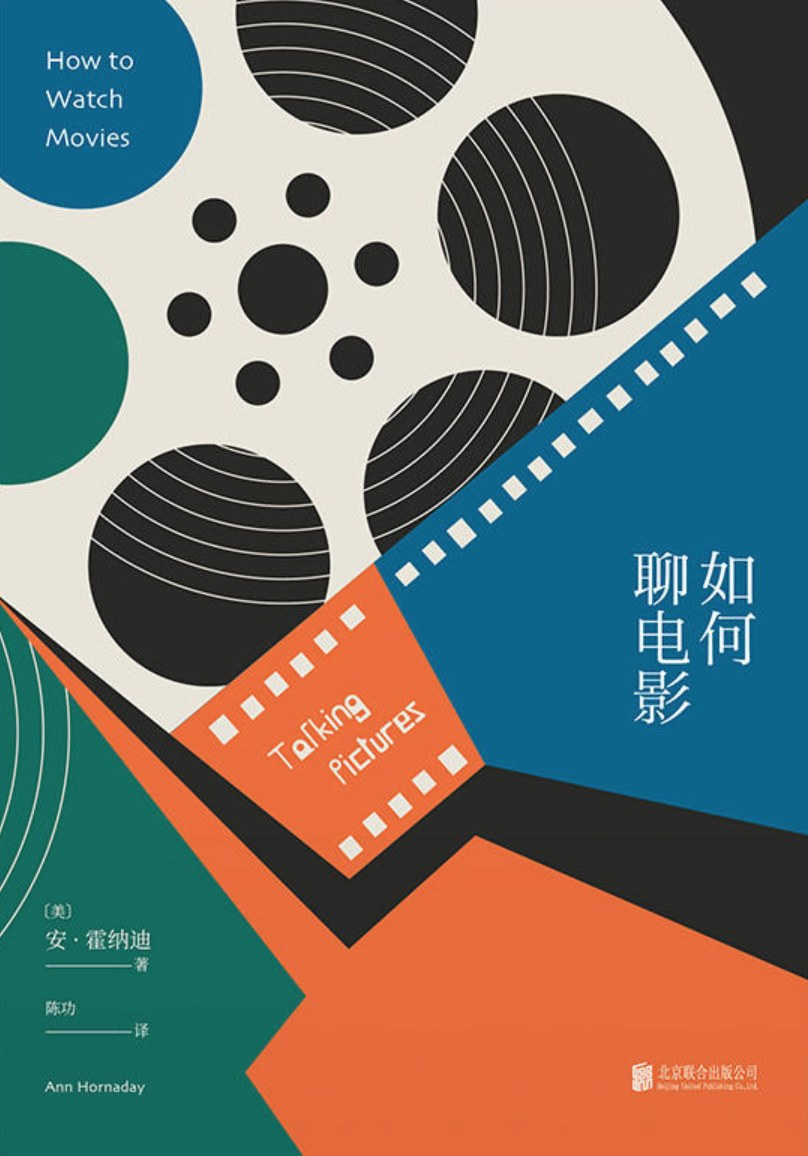电影是什么H1
作者从影评人的角度,给我们说了从哪些维度去给电影做出评价,里面也窥探出一步电影的制作过程。我深感导演的强大,从剧本剧情走向,到确定基调色调选角,再到每一个镜头的位置和移动方向,如果是一个追求细节导演,这些都是需要一一去确认的。可想一部伟大的电影就是一群人的呕心沥血,是一个艺术品。
与文字艺术相比,电影不如文字直白,用视听语言去表达。视听语言非常考究导演对生活的观察,用声音和画面去传递信息,例如蓝色表达忧郁、手持摇晃表示紧张不安、特写突显人物情感,这些都是利用人类潜意识对食物的本能反应,做到潜移默化去表达。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一个电影好看,但又道不出它具体的原因,只觉得电影看起来很舒服、恰当好处。
书中讨论到某些导演追求细致写实,那什么是细节最多,真实生活。如果真实生活就是最高级的电影,那不如直播像楚门的世界一样,但这不实际,电影的时长有限。所以电影是把一段故事浓缩到有限的篇幅以内,要做到特点突出、详略得当,完全写实是平淡,需要适当用颜色标注重点。而这些视听语言技法就是导演所要掌握的。
书本的主体是冗长的,说到每一点都有大量的讨论和例子,不是想要拍电影的话都很难详细读下去。评价电影的维度有:剧本、角色塑造、对白、基调、主题、视角、服装、特效、摄影…
摘录H1
- 做一名“影评人”观众,首先要在精神上做好准备。你一定要放空,放下一切抵触、偏见或者任何影响你精神集中的东西,因为这些都可能阻碍你彻底投入到影评工作当中。理想情况下,电影应该能释放足够的魔力,让你没法在观影的过程中胡思乱想,直到片尾字幕开始滚动时,大脑才会切换到影评人状态。
- 通常来说,一个好的剧本应该对环境和角色有精准细致的描绘。但涉及特定的镜头角度、剪辑、风格化呈现,就和剧本无关了,这些内容都是由导演和影片创作团队决定。事实上,如果剧本带有大篇幅的描述性段落,有时反而会打击电影制作者的积极性,因为有些制作者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打造精彩的故事和生动的角色,而不是全程被过于热心的编剧牵着鼻子走。更何况在大部分情况下,一旦影片进入正式制作阶段,编剧根本就不会再参与其中,而且他的剧本很可能会被一群“剧本医生”(script doctors)、导演甚至片中的明星演员重写。
- 剧情只是说事,故事是在讲意。剧情是机械复述,故事是表达感情。
- 曾为《出租车司机》《愤怒的公牛》(Raging Bull)等经典电影操刀的保罗·施拉德(Paul Schrader)说过,一部好的剧情片“应该有大约五句好台词和五句经典台词。超过这个数量,就会让人觉得啰唆和不真实。观众就只是在听大段的台词,而不是在看电影”
- 在欣赏这些电影时,看和听同样重要,因为它们在视觉和听觉上都在传递大量的信息。林克莱特就曾经对我说过:“重要的不是具体的台词,重要的是演员的表达,是其中的含义。”而传递含义是一种接触性运动:对白不只是角色说的话,它本身也是一种动作,既然是动作,就应该有动力和推力。对白的每一个字眼都很重要,都要经过深思熟虑、精心打磨,都应该包含多重含义。
- 判断基调这部影片的情绪是什么?它是想逗人发笑,是严肃正经,还是两者兼具?电影制作者是否同情角色?他是从角色的角度思考,还是站在一定距离外观察?基调可能是编剧工作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部分,这也是一个几乎无法定义的概念。
- 有时我们看到一部电影就知道它的基调,但更多时候,我们只有通过感觉,抓取电影制作者在每一句台词、每一个眼神、每一幅画面、每一段声音中传达的细微信号,才能知道影片的基调是什么。基调是一部电影的情感音调,是电影的情绪和格式塔。基调是一部电影的美学法则,决定了观众能否从影片的基本剧情中获得更深层的含义。基调可能是由我们的视听体验构成,但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感觉。
- 电影主题影片的故事是否另有深意?电影是否引发了我的后续思考?影片是否还触及历史、现代生活、人性、希望、绝望等话题?电影展现的内容有两种:一种是表面的故事,一种是实际的内涵。有些电影纯粹是为了帮助观众逃避现实、获得娱乐,并不会触及深层内涵或者道德问题。而有些电影即便披着奇观化的外衣,也会通过潜台词、隐喻、视觉暗示等方法超越基本的叙事,展开深刻的讨论
- 表面上看,《正午》是一部典型的小镇警长式西部片,讲述加里·库珀(Gary Cooper)饰演的警长努力在镇上寻求帮助却无人响应,最后只能孤身对抗犯罪团伙的故事。但仔细分析,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在控诉民粹主义盛行下的政治怯懦。表面上看,《机械战警》(RoboCop)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火爆动作片,讲述一个被改造成机器人的底特律警察如何惩恶除奸,但往深处挖掘,它其实是在反映人性,反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型企业对社会无所不在的控制,以及大男子主义文化的构建。表面上看,充斥着怀旧音乐与时代细节的《不羁夜》(Boogie Nights)是对七十年代洛杉矶色情业工作者的淫猥一瞥,但实际上,它讲述的是个人在站队文化中寻找自我,反映人们的价值观与身份是如何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变化,以及电影媒介本身的浪漫与脆弱。所有这些含义都埋藏在对白与画面之下,而一个好的剧本要能让观众透过银幕上的内容发挥想象,挖掘其中的深意。
- 最好的银幕表演应该能在“表现”与“克制”之间达到超常的平衡,也就是说,既要透明到能让观众瞬间了解角色,又要内敛到让观众好奇角色下一步会怎么做。你可以留心演员在不说话时,脸上是否会失去一些神采;或者当另一位演员在说话时,他能否像注意自己的台词一样注意对方的台词。
- 在我采访罗伯特·德尼罗时,他非常热情大方,回答起问题来滔滔不绝,但不出意料,谈及他表演的秘诀时,他就没有那么坦白了。(“不要说出去”是他的一句口头禅,而且他自己也是个守口如瓶的人。)当我和其他电影人聊起罗伯特·德尼罗时,“克制”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。他们都认为,不管角色有多愤怒、肢体语言有多强烈,他总是会保留一些关键的东西不让观众看见。
- 如果说表演是电影的原始工具,那么选角就是对生拇指——没有对生拇指,再好的工具也是徒劳。选角的艺术离不开经验、品味、直觉、风险、讨价还价,还有纯粹的运气。首先,电影制作者必须认可演员过去的作品和他或她塑造过的银幕形象。
- 《总统班底》最终被两位巨星的星光笼罩,但依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——这不是一部哗众取宠的好莱坞俗片,也不是以明星的人气和性吸引力为卖点的兄弟片,而是一部干净利落、制作精良的惊悚片,而且霍夫曼和雷德福都让自己彻底融入整个故事当中。当超级巨星碰巧又是顶尖演员时,就能产生这样的效果。而放在今天,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只会越来越难,因为通过社交媒体和TMZ这类全年无休的八卦网站,影迷与电影明星的距离已经前所未有地缩短。
- 可是,评价演员和他们的表演本来就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,因为他们呈现在银幕上的只有他们自己。了解我们对某些演员的主观好恶,其实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他们的工作本质,即他们只是一个诠释工具,观众是通过他们来理解影片故事的意义与情感。演员在表演中仅有的工具就是他们的自然存在——他们的脸、身体和声音——和他们的精神活动,通过思考、分析、想象,来把角色演活。
- 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注意,但电影的艺术设计一直在帮助我们感知和理解电影,并在视觉、精神乃至潜意识上影响我们。
- 片中的颜色是浓烈、华丽、明显,还是朴素低调,几乎没有存在感?这些色彩是在帮助叙事,还是衬托、暗示当下已经很明显的情绪和信息?颜色可以决定一部电影,打造出一个充满象征意义和情感的世界,触发观众不自觉的反应。颜色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。事实上,艺术指导在读完剧本后做的第一件事情,通常就是确定电影的色调(palette)
- 颜色可以决定一部电影,打造出一个充满象征意义和情感的世界,触发观众不自觉的反应。颜色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。事实上,艺术指导在读完剧本后做的第一件事情,通常就是确定电影的色调(palette)
- 角色视角我们进入了哪个角色的世界?最好的艺术设计不仅能帮助观众理解主角的视角,还能进入主角的视角。
- 电影一定要尽量多给观众一点儿信息,用画面和信息淹没他们。如此一来,一部电影便可以重复欣赏,影迷每次重看都会有新的发现。
- 服装不仅能体现一个角色的阶层地位、家庭背景,甚至宗教和性取向,还能传达角色隐秘的欲望和追求的形象。用伊利亚·卡赞的话来说,服装应该“能表现角色的灵魂”。但是服装也能呈现电影明星最迷人、最具诱惑性的一面,让观众获得逃避现实的快感和感官上的愉悦
- 精彩的视觉特效需要在想象力的基础上精心编排,以及耗时耗力的制作和执行。但是最终呈现给观众的时候,视觉特效应该趋于隐形
- 艺术设计最基本的作用,是给观众带来观影快感,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满意的视觉体验。电影一直都是一个提供间接体验、满足窥探欲和逃避需求的媒介。
- 在好莱坞的“黄金时代”,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,摄影师追求的是摄影的透明性,强调故事的简洁清晰,并把最华丽的灯光打在电影公司最宝贵的财富——电影明星的身上。在四十年代,随着电影制作者越来越多地受到德国表现主义和战时摄影的影响,电影的灯光也开始富有情绪和自我表达性。在六十和七十年代,法国新浪潮、美国街头摄影和纪录片制作开始大受关注,摄影也变得更具示意性,更加晃动不安,与此同时,质感粗粝、并不完美的胶片也开始大行其道。
-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,低光摄影都应该遵循同样的标准:隐藏起来的视觉信息要能进一步将观众吸引到叙事当中,而不是迫使他们吃力挖掘。不管阴影有多么强烈的情感效果,都应该时不时用灯光进行平衡与消解,避免我们观影时像在浑水中游泳一样痛苦不堪。
- 通过上述例子,我们可以看到镜头运动是如何营造活力感、宏伟感、历史感和紧张感。这些镜头之所以备受影评人及其他电影制作者的欣赏,是因为这其中饱含冲破窠臼的野心,而且这其中的技术难度令人咂舌,不仅需要演员在一个镜头中准备好所有的台词与动作,还需要通过高超的技术来隐藏阴影、镜像反射以及麦克风等拍摄该镜头时所需的技术设备。不过,真正高超的摄影还是和炫技有区别的。不管一部电影使用了哪些视觉花招,都不能妨碍观众对影片故事和角色的关注。下次你看到两个角色说话时,如果镜头像跳塔兰泰拉舞一样绕着说话者疯狂旋转,不妨问问自己:这样的镜头除了让你无暇关注角色的对话内容,到底还有什么意义。
- 远景也叫“全景”(wide shot),全景镜头视野非常广阔。如果全景镜头中有人,那么人物通常是处于次要位置,镜头中的自然环境或者人造环境才是主角。因为远景镜头能够传达很多关于时间与地点的信息,所以它们通常都是用来作定场镜头,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。但是远景镜头也可以用来达到非常反直觉的效果,
- 但是宽屏画幅并不只适合拍风景,事实上,用它来呈现画面内的张力和运动、为电影环境打造细节感,要比拍风景有趣得多
- “迈阿密在我的记忆中就是非常广阔、非常空旷,有深绿色的植物,也有耀眼的阳光、碧蓝的天空。”詹金斯说,“但我依然觉得自己孤身一人,处境艰难。”为了在宽屏下捕捉这种与世隔绝的感觉,詹金斯“想给奇伦(片中男主角)大量的空间,但他却不知道这些空间对自己有什么意义……他想去哪里都可以,但他依然选择困在自己的世界之中”。2010年,在拍摄西部片《米克的近路》时,导演凯莉·赖卡特使用了接近正方形的1.33∶1画幅,让人联想起安东尼·曼(Anthony Mann)和霍华德·霍克斯的早期西部片中方方正正的画面。凯莉·赖卡特的做法既是致敬电影前辈,也是为了捕捉影片主角的视角。因为这是一群前途渺茫的迁徙移民,所以他们不敢想未来。“在宽屏画幅下,你看得到明天也看得到昨天,”影片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后,赖卡特向记者解释说,“但在方形画幅下,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的当下。”
- 广角镜(wide lens)的景深浅,也就是说在广角镜头下,前景中的演员是唯一被对焦的对象,背景则是处在不同层度的模糊之中。相比之下,窄角镜头(narrow lens)或叫长焦镜头(long lens)则能打造更深的景深,让画面中的一切都清晰锐利地显现出来。
- 两种画面风格都没有问题,当然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好反直觉式的色彩选择,比如用充满生机与欢乐的颜色去展现一个绝望的场景,或者在拍摄一部历史剧情片时,不用传统的高贵、光鲜的色系,而使用更为粗糙和写实的颜色。
- 他们看的这部电影值得拍吗?回答这个问题前要分清楚情况。如果一部电影就是为了追求酷炫,那么斥责它内容不够严肃,或者艺术上缺乏野心,未免也太过吹毛求疵。不过,如果电影制作者用老套的剧情、千篇一律的角色、毫无诚意的制作来糊弄观众,指责他们骗钱倒也无可厚非。另一方面,刻意追求严肃和“内涵”的电影并不见得就是好电影。像这种企图通过探讨人性来故作深沉的电影,我看得太多了,结果只会让人觉得这类制作肤浅无聊、自作聪明、陈腐不堪,而且令人生厌,因为实在是太矫情了。不管一部电影的主创人员是想拍简单的娱乐片还是严肃的艺术片,都无可厚非,只要成片能让观众感受到诚意和原创性,能够反映出一定的专业精神,它就是一部合格的电影。如果一部电影让你感觉制作人员对观众满不在乎,完全不考虑观众的需要与口味,那这样的电影只会让人坐立不安。如果一部电影让人感觉轻松愉快,觉得它内容丰富,很对自己的胃口,即便这只是一部简单的喜剧或者动作片,也能让人获得满意的观影体验